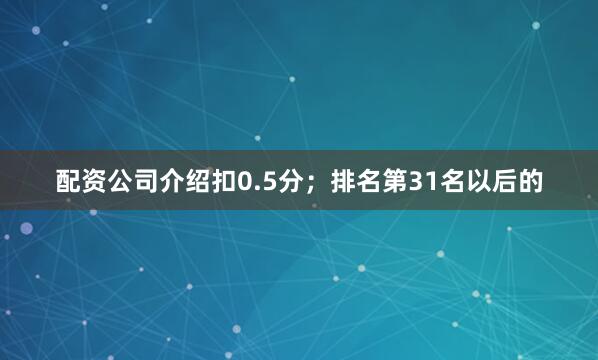你有没有想过,那些穿军装的人下班后,他们的家属孩子过着什么样的日子?对很多从部队大院里长大的人来说,那不是普通的居民区,是个能把“保家卫国”和“柴米油盐”揉在一起的地方。现在提起部队大院,有人说那是老黄历,可为啥总有人翻出来念叨?

要说部队大院的来头,得从新中国刚立稳脚跟那会儿说起。那会儿国家要解决军人和家属的生活问题,又得让军人们能随时响应任务,干脆在军区附近盖起一片“大社区”。北京玉泉路、南京紫金山脚下、沈阳东陵边上,这些地方的大院最集中,出门就是营区,买菜上学也不耽误。说是“大院”,里头啥都有:幼儿园的滑梯、学校的铃声、医院的消毒水味混着小卖部的糖果香,连球场边的老杨树都是看着孩子们长大的。那时候的人都说,进了大院门,日子就像上了双保险——外头是战场,里头是家。
大院里的房子可不是随便分的。士兵住集体宿舍,上下铺挤得跟沙丁鱼罐头,晚上说梦话都能串到隔壁床;连长营长能分到两居室,厨房厕所都齐活;要是将军级别的,可能住上带小院的独栋,葡萄架下能摆棋盘。但规矩严归严,也有通融的时候。记得有个老兵说,他当年当班长时,班里有个新兵弟弟生了病,家里穷得连药钱都凑不齐,连长特批他搬去单人间,方便照顾弟弟。后来那弟弟病好了,跟着哥哥在大院里跑,见人就喊“恩人连长”。这规矩看着硬,里头却藏着热乎气——你肩上的责任越重,住的地方越宽敞;你要是难,大家伙儿也不会袖手旁观。

要说大院里最热闹的,还得数过节。1975年中秋,有个大院组织包饺子,从连长家属到新兵的妈都来了。饭厅里红灯笼晃悠,锅炉烧得滋滋响,蒸汽糊了窗户。孩子们蹲在灶台边偷饺子,被炊事班老王追得满院子跑。有个奶奶包了个带硬币的饺子,说是“幸运饺”,结果被刚退伍回来的老班长吃到了,他举着饺子直乐:“当年在前线啃压缩饼干,哪想到能在这儿碰着这福气!”周末家属们凑一起做饭,你端盘红烧肉,我带碗腌黄瓜;孩子们在操场玩“抓特务”,嘴里喊着“缴枪不杀”;退役的老兵回来看老战友,蹲在墙根抽着烟,把当年的事儿翻来覆去讲——这哪是兵营?分明是个放大的家。
要说这院里最“隐形”的功臣,还得是军属里的女人们。1978年夏天,陈团长被派去外地执行任务,他爱人张姐在大院医院当护士。那会儿赶上传染病闹得凶,张姐三天三夜没合眼,给病号喂药擦身,还变着法儿熬粥。有个小战士发烧说胡话,喊“妈”,张姐就坐在床边拍他背,跟哄自己儿子似的。后来陈团长回来听说这事,直叹气:“我在前线操心任务,她在后方操心一院子人——这哪是我在保家?是她在给我兜底。”这些女人们没穿军装,可大院里的每扇窗户亮着的灯,每张饭桌上热乎的菜,都是她们熬出来的。

现在的部队大院变了。老楼拆了盖新楼,孩子们能去市区上重点学校,军属们也能在外头找工作。可有些东西没变:退役的老兵总爱晃回来,蹲在老槐树下跟门卫唠嗑;赶上紧急任务,大院里的广播一喊,家属们自发帮忙搬物资,比下命令还利索;就连新来的年轻军官,都爱听老人们讲“当年那谁谁谁”的故事。有次跟个退休的老营长聊天,他说:“现在住的小区,门对门都不认识;可在大院里,就算搬走十年,碰着面还能喊出小名。”
现在再路过老部队大院,墙皮可能掉了,树倒是更粗了,可要是碰着个遛弯的老兵,他准能跟你唠半宿,从当年谁偷了食堂的饺子,到如今孙子考上军校——你说这大院,哪是几栋房子?分明是本翻不完的书。

(免责声明)文章描述过程、图片都来源于网络,此文章旨在倡导社会正能量,无低俗等不良引导。如涉及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,请及时联系我们,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内容!如有事件存疑部分,联系后即刻删除或作出更改。
手机上买股票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炒股配资理财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
- 下一篇:没有了